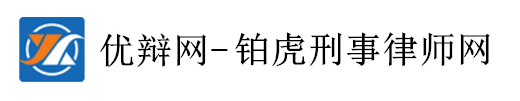【内容提要】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完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律师会见权方面体现了对律师有效辩护权的尊重与保障。但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有改进的空间。为了有效地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充分实现,本文拟从安排会见机关的中立化和救济途径的完善化两个方面进行机制建构。一方面,将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由非隶属于侦查机关的其他机关负责和实施,实行侦羁分离。另一方面,应当将违反会见权所取得的证据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通过司法解释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程序性救济的权利。
【关键词】会见权 有效辩护 侦羁分离 程序性制裁
近年来全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的比例不足30%,有的省甚至仅为12%。全国律师现已超过22万人,但2010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不足3件,有些省份甚至不到1件,且其中还包括法律援助案件。⑴在北京,这一比例更低。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称,“一年2万件刑事案件,有律师代理的不到500件,只占2.5%,其中很多还是政府指定律师辩护的。”⑵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率低显而易见。考察背后的原因,可能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能否请得起律师有关,也可能与一直困扰刑辩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三大问题有关。试想,如果作为刑事辩护律师连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受到阻碍,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何在。
一、当前侦查机关排斥会见权的表现与动因
侦查机关拒绝律师实现会见的常见形式有:以侦查保密为由拒绝安排会见;以不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安排会见;以不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对会见申请均要求履行批准程序;有的虽安排会见但一律派员在场,使得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会见权无法落实,会见流于形式;有的限制会见次数和时间,实践中多数地方看守所限定只能会见一次或两次,每次会见的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有的限制会见内容,要求会见不得涉及案情,甚至要求律师会见前提供会见内容提纲,会见时交流不得超过提纲范围。那么,为什么侦查机关如此排斥律师的会见权呢?
主要是证据收集的需要。侦查机关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没有根本改观。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依靠心理攻势来促使被追诉人供认犯罪事实,而被追诉人与律师的会见则恰恰能在客观上淡化、抵消侦查机关可能营造好的心理压力,给予犯罪嫌疑人很大的精神支持,对于一些真正的罪犯而言的确会成为其抗拒侦查、拒不交代的心理基础。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在会见辩护律师后精神面貌判若两人、大幅翻供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侦查机关对于会见权的忧虑并非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权规定的不足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完善辩护律师会见权方面吸收了律师法的规定,体现了控辩平衡以及对律师有效辩护权的尊重与保障。但是,鉴于目前会见权在实践中运行的实际遭遇和侦查机关的天然排斥,新《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不足。
(一)见面的次数、时间没有细化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但是并没有规定会见的次数和时间。在实践中,有关机关限制会见的次数和时间的做法并不少见。有的省份限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得超过两次,有的省份甚至限定会见嫌疑人不得超过一次,且不得超过30分钟。⑶毫无疑问,如果限制会见次数以及会见时间,就无法保证律师向被追诉人全面了解案情,听取其意见或者为其提供有效咨询,也无法保证随着案情的发展,律师与被追诉人继续交流。这种做法使得律师会见权无法落实,这不仅与立法本意不符,而且与联合国有关人权文件的相关规定相悖。基于此,有理由认为,只要律师符合会见的条件,看守所均应在法定时间内安排会见;只要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内,均不能限制律师会见被追诉人的时间。如果因为侦查机关讯问与律师会见的时间发生冲突,或者会见室数量的限制等合理原因导致律师会见“不充分”,应当在这些原因消失后再次安排会见。 (二)易被曲解的“不被监听” 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条款有利于保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秘密交流权”,是我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体现。但在实践中,对这一条款含义的理解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解读,即“容许在场说”和“排除在场说”。持“容许在场说”的论者认为,为了防止辩护律师滥用会见权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风报信或者教唆翻供,同时也为了保障辩护律师的人身安全和防止在押人员脱逃,应当将“会见不被监听”理解为禁止监听但不排除有关人员必要的“在场”。持“排斥在场说”则认为,从《刑事诉讼法》加强对辩护律师的辩护权的立法精神来看,“不被监听”在于维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谈话的秘密性,从而降低当事人的顾虑,有利于辩护律师全面、准确把握案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被监听”与允许有关人员“在场”是矛盾的,并且,也与国际通行的惯例不符。根据以往的执法实践,在场的侦查人员经常会随意打断、甚至禁止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讨论案情,从而导致这一环节的有效辩护权无法真正落实。⑷因此,落实“会见不被监听”必须禁止有关人员“在场”。事实上,分析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沿革、考察立法本义以及参考国际惯例,不难得出“会见不被监听”含有禁止有关人员“在场”的含义,理由有二: 第一,“会见不被监听”禁止有关人员“在场”符合立法本义。新《刑事诉讼法》删除了1996年以来《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律师会见时有关人员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这就使得侦查人员曾经获得的“在场权”在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已没有明文的法律依据。如果不允许监听却允许在场,那么“不被监听”的规定就名存实亡。 第二,“会见不被监听”禁止有关人员“在场”符合国际一般准则。在西方国家中,普遍规定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在会见时的秘密交流权,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羁押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可以单独与辩护律师会见;英美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讯问前、讯问后和讯问过程中与辩护律师秘密会见的权利;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指定的律师可以在秘密的条件下会见被拘留人”;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单独会见辩护人,会见内容保密”;荷兰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律师与委托人“可以单独交流和通信”。⑸ “会见不被监听”最大限度地降低有关机关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流的监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如何在实现这一交流过程私密性的同时又能排除这一过程的安全隐患呢?对于这一问题,国际上早有成熟的做法,即对会见过程进行必要的监视,但这种监视不能影响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谈话内容的保密性。这一点为联合国的相关文件所确认。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93条规定,警察或者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之间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得见的范围以内。⑹ 公安部也在其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2条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回应:“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不得监听,不得派员在场。”严格执行“会谈不被监听”还应当遵守其所派生出的两条规则:第一,侦查人员不得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前通过各种方式如事先警告犯罪嫌疑人等来限制谈话内容;第二,侦查人员不得在会见后追问谈话内容。以上两条规则所规制的行为实质上是侵犯会见权行为在时间上向前和向后的延伸。 (三)无法实现的“核实证据”与不平等的“录音”、“录像”权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这意味着,会见时律师可以就有关指控事实及相关证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要时还可将有关证据出示给对方,让其辨认,与其核实。这使得会见权的行使具有实质性。但是,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如果其不能向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其会见权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架空。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都会作笔录,但仅作笔录不一定能全部记录下谈话内容,必须以录音、录像辅以帮助;这也可以防止个别犯罪嫌疑人歪曲律师的会见记录或者个别在场侦查人员指控律师有诱问、包庇的谈话内容等违法行为。因此,应当允许律师享有当场的录音、录像权;再者,2012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197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将对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告知情况应当在录音、录像中予以反映,并记明笔录。”鉴于律师是与控方相对应的辩方的被委托人,从控、辩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诉讼权利对等来说,理应享有同等的可以录音、录像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有权代理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只有赋予律师有录音、录像权才能把犯罪嫌疑人的控告、申诉的谈话内容通过录音、录像固定下来,律师才能在会见后将其作为代理控告、申诉的证据材料移送。⑺ 三、对会见权限度的平衡
有学者认为,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的时间由“第一次讯问后”提前到“第一次讯问”,从而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第一次讯问时即可获得律师帮助留下了解释的空间,即犯罪嫌疑人自第一次被讯问时起,理论上委托的律师就有权会见,⑻即有首次讯问在场权。然而,考虑到这一阶段的侦查利益,律师的首次讯问在场权必须受到限制,这是因为,在首次询问时,往往是对侦查权至关重要的时候,正如法国著名侦查学家艾德蒙·费加尔所言,“侦查工作的头几个小时,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失掉了时间,就等于蒸发掉了真理。”⑼侦查机关在第一时间控制犯罪嫌疑人,无论通过讯问获得的是有罪供述或者无罪辩解,还是通过犯罪嫌疑人对同案犯罪嫌疑人、物证以及犯罪现场等的辨认,对于侦查机关发现案件线索、追捕同案犯罪嫌疑人,调整侦查方向都至关重要,实证研究表明,初次讯问中的认罪率高达87.93%。⑽此外,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如果不及时收集,即使没有受到人为的损毁,也有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湮灭。因此,在此阶段如果一味强调会见权,一方面可能导致丧失侦查时机,导致重要证据灭失,另一方面容易打乱侦查机关的侦查策略和部署,使其侦查效果大打折扣。⑾并且,在秘密会见的前提下,辩护律师在这一阶段存在违反职业伦理道德底线违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甚至教唆、串供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其他阶段。对于这种行为,虽然可以通过对律师的纪律处分或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进行制裁,但是由于前述保障交流私密性的需要而禁止监听手段的运用,因此导致了私密会见中的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与依法追究律师滥用会见权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在会见权和侦查权之间进行平衡。由于律师会见与侦查讯问的对象具有同一性,因此同一个犯罪嫌疑人在同一时间不可能既接受讯问又会见律师,必然存在先后顺序。考虑到首次讯问时侦查权的重大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率的实现,对会见权的限制是必要,也是必须的。因此,虽然许多国家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即可介入并且享有系列诉讼权利,但当过度介入威胁到侦查效果时,也必须受到限制,例如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58(6)条规定,只要被拘押人提出请求,可以允许其向律师咨询,但当其被怀疑犯有严重可逮捕罪行,则由警督以上级别的警官批准后可延迟这一权利。⑿
四、对会见权保障机制的建构
(一)安排机关的中立性
司法实践中,虽然法律规定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不被监听,但是,实际做法是侦查机关派员在场。派员在场的主要目的不是防范犯罪嫌疑人逃脱,而是监督谈话内容,避免讨论案情。据调查,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在场率高达75.4%,而且双方谈话11.4%是被侦查人员打断而结束。⒀ 目前,羁押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场所是看守所,而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有些看守所甚至承担着部分破案的任务。据公安部2006年的一个统计,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破获的案件占12.5%。⒁在这种情况下,看守所与公安机关有共同的立场,因而充分会见不被监听的立法精神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实现。我国将犯罪嫌疑人羁押和讯问场所交由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控制,即实行侦羁合一制度,这为侦查人员限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便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将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由非隶属于侦查机关的其他机关负责和实施,⒂实行侦羁分离制度,对于相对中立的羁押机关来说,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没有任何行政上或其他利害关系,一个不关心案件结果的中立机关,无论是侦查人员的讯问还是律师的会见,只要是按照法律规定行事,均不会与其产生什么利害冲突,没有抵触律师会见的动力,也不会产生协助刑讯逼供的动力,也才能真正保障“秘密交流权”的实现。⒃ (二)法定后果:毒树之果 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增加规定:辩护人认为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该规定将权利救济的主体定为检察机关,契合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法律监督者地位,但是检察机关兼有控诉者与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其能否有效履行权利救济的职责,尚存疑问。如果辩护人提出申诉、控告以后,检察机关不审查或不及时审查,不处理或不公正处理,或者要求办案机关进行纠正而办案机关不予纠正应如何处理,该条规定并未提供明确答案。⒄ 目前,我国对供述的排除还仅限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的情况,对于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限制及剥夺会见权的情况尚无法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规制。因此,应当将违反会见权所取得的证据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通过司法解释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程序性救济的权利,即通过程序性辩护的诉权请求开启程序性裁判程序,对侦查人员侵犯会见权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宣布侵犯会见权所获得的证据材料以及以此为线索获得的材料为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⒅这样才能对侦查机关变相“监听”会见产生阻却效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朱磊:“于宁委员:建议提高刑案律师参与率”,载《法制日报》2012年3月11日。 ⑵慕平:“两万刑诉案 律师仅代理2.5%”,载《新京报》2012年3月9日。 ⑶肖周:“刑诉法、司法解释与律师诉讼权利保障”,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⑷陈学权:“‘会见不被监听’对律师职业伦理的挑战及应对”,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11期。 ⑸李红:“比较法视野下的律师会见权法律保障与制约——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为参照”,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⑹汪海燕:“合理解释:辩护权条款虚化和异化的防线”,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6期。 ⑺周国均:“控辩平衡与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l期。 ⑻汪海燕:“一部被‘折扣’的法律——析《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 ⑼[前苏联]拉·别而金著:《刑事侦查学随笔》,李瑞勤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⑽刘方权:“认真对待讯问——基于实证的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 ⑾陈学权:“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5期。 ⑿陈光中、汪海燕:“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⒀朱桐辉:“会见权的中国困境与再改革”,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⒁黄卓娅、梁霞:“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的原因及对策”,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⒂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⒃郑金玉:“律师会见权实现的现实难题”,载《前沿》2009年第8期。 ⒄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45—46页。 ⒅闵春雷:“论侦查程序中的会见权”,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 |
|
|